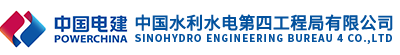十年青春里,我的水電風電夢 |
|
|
|
|
清晨的車間還帶著夜的涼,我蹲下身,指尖碰了碰待加工的鋼板——這觸感,我熟了十年。從2015年背著工具箱走進來,到現在身后跟著幾個年輕徒弟,我手里的大小扳手、尺子都換了好幾茬,磨破的帆布手套能湊成一打,可每次拿起圖紙時,心里那股熱乎勁,從來沒涼過。他們都叫我“官班長”,可我更愿意說自己是個冷作工:冷的是鋼鐵,熱的是琢磨活兒的心,還有藏在鐵件里的那個夢 ——水電的奔騰、風電的旋轉,我得為它們拼出“筋骨”。 剛入職那陣,學的第一道工序就是風電塔筒組對,那會兒我連風電塔筒組對的基礎流程都摸不著門道。看著一堆弧形筒節、法蘭盤和加強筋,不知道該先對哪個基準,更分不清拼接時的錯邊量該怎么控制。師傅站在旁邊,看著我把筒節拼得歪歪扭扭,螺栓孔對了半天都對不上,沒罵我,只把一塊風電塔筒的法蘭盤放在我面前:“這玩意兒要裝在幾十米高的塔筒頂上,連著葉片和機艙,差一毫米,風機轉起來就可能晃,時間長了整臺設備都得出問題。冷作工的眼,得比激光準直儀還尖;手里的找平桿,得比水平泡還穩。” 那天我練到車間只剩我一個人,反復用卷尺量筒節的圓度,用撬棍一點點調整錯邊,胳膊被冰涼的筒壁硌得發紅,額頭上的汗滴在法蘭盤的螺栓孔里,暈開一小片水漬。可當最后一組筒節拼完,用水平儀一測——圓心偏差剛好在標準范圍內,法蘭面的平面度數據也不差時,突然就懂了:我手里的活兒,不是簡單的“把鐵筒拼在一起”,是要托著“讓風轉起來、讓電送出去”的念想。那時候的夢想,小得具體:明天能把組對的速度提快點,下次能獨立完成一節塔筒的拼接,不讓師傅再跟著操心。 后來跟著班組去水電工地支援,任務是安裝水電站的閘室埋件。站在剛澆筑完的閘室基坑里,抬頭能看見上方橫跨的吊機臂,腳下是還帶著水泥潮氣的預埋槽道,身旁堆著一排排沉重的錨筋和鋼襯——這些都是要牢牢固定在混凝土里的“根基”,得我們親手校準、焊接、澆筑。 老師傅踩著腳手架爬上來,指著閘室兩側的預留位置說:“咱現在裝的這些埋件,將來要托著閘門的軌道,閘門升降全靠它受力。要是位置偏了一公分,閘門要么卡殼關不嚴,要么漏水沖壞壩體,下游的安全全在咱這手里的準頭里。” 我蹲在預埋槽道旁,伸手摸了摸剛焊好的錨筋焊點,金屬的余溫混著工地的塵土味撲過來。正好趕上上游水庫開始少量蓄水,遠處傳來水流過導流洞的轟隆聲,老師傅說:“等這閘室完工,閘門一落,水能存住,機組才能轉;閘門一提,水能泄洪,下游也安全。咱裝的這些‘鐵疙瘩’,看著不起眼,卻是水電的‘腳’,沒它,啥都轉不起來。” 那一刻突然鼻子發酸——原來我這雙沾著水泥灰、磨出繭子的手,也在給“讓水發電、保一方安瀾”的事搭著架子。 夢想這東西,在工地上從來不是掛在嘴邊的話,是用水平儀反復校準埋件時的較真,是焊接錨筋時盯著熔池的專注,是用全站儀測完位置“誤差在兩毫米內”的踏實 ,每一下調整、每一個焊點,都是在給水電的“筋骨”扎牢根基。 三年前當上班長,肩上的擔子沉了些。有個年輕徒弟總跟我抱怨:“班長,天天對著這些筋板、校尺寸,干的都是‘埋在地下’‘藏在墻里’的活兒,有啥意思?” 我沒跟他講大道理,午休時特意把他帶到車間閘門埋件的成品區,指著堆在一旁的水電閘門埋件——有帶著密集錨筋的門槽鋼襯,有銑得平整光亮的止水座板,還有鉆滿定位孔的閘門連接板。 “你別覺得這些鐵件不起眼,” 我蹲下來,指尖敲了敲反軌上的焊接坡口,“這組埋件是要裝在滇中引水的閘門井里的,將來閘門升降時,就順著咱裝的這些埋件上行走,止水座板得嚴絲合縫接住閘門的止水帶,差一毫米,就達不到封水效果”。我又拿起測量儀器指著眼前制作好的產品:“你看這面的平整度,咱用水準儀測量了八遍才合格。將來閘門關上,止水帶壓在這上面,才能擋住水。咱干的不是‘埋著藏著’的活兒,是水電的‘地基’——沒有這些埋件把閘門穩住,水發不了電,防洪也沒保障。你說沒意思?咱的扳手擰緊一圈,就是給千萬家的光明和安全多上一道保險,這咋能沒意思?” 有人問我,十年守著車間,不膩嗎?我指了指手上的老繭:“你看這繭子,都是大小榔頭磨出來的;你看那些成品,是咱們一榔頭一焊槍敲出來的。水電要穩,風電要牢,咱冷作工的活兒,就是給這些大家伙‘打底’。我這十年青春,沒浪費在虛頭巴腦的事上,都融進這些鐵件里了,它們去了大江大河,去了高山曠野,替我看著水怎么發電,風怎么轉,這就是我的夢想。” 現在每天開工前,我還是習慣先摸一摸鋼板。涼的鐵,熱的夢,十年沒變。接下來的日子,我還想帶著徒弟們多琢磨些新活兒,把圖紙看得更細,把產品裝配尺寸做得更精準。畢竟水電的水還在流,風電的風還在吹,我的夢,還在每一次精準對接的金屬縫隙里閃著光呢。 |
|
|
|
| 【打印】 【關閉】 |